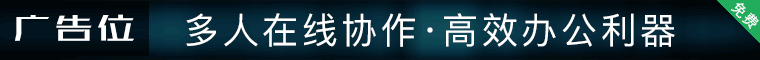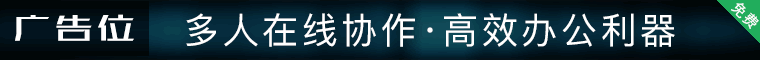美食与人生一样,大都在于熬
人们执着于爱恨,困囿于生死,
人们执着于爱恨,困囿于生死,
到头来都不过是海面上的幻影一场。
只有用心吃下的一蔬一饭,是我们的信与命,照见来路与归途。
照见来路与归途。
文|罗楠
▲主播/夏忆配乐/赵照-声律启蒙
“三月吃芦笋,用开水焯一下就好,
像生活,愈简单愈清白。”
……
我和远在加拿大的表姐,
常常隔着茫茫地域,和颠三倒四的时差,
在微信中互换着如何把食物吃进肚子里的心得。
表姐是这几年才爱上了美食与厨房。
曾年少轻狂,走遍了山川湖海,
收拾了小半生的月与花香,滔滔韶光,
最终回归至市井中的人间五味。
大抵“琉璃世界白雪红梅”的娇俏女儿,
终有一刻,沾了人间烟火,
脂粉香娃敢于“割腥啖膻”,
落到一蔬一饭一餐一眠,
这生活,才显出踏实的况味。
所谓万千美物,落肚为安。
红尘百戏,终有尘埃落定的一天。
吃喝向来是大事,为人生一欲,亦是人生乐事,
乐至极致,便可成为近乎艺术的趣味。
是那个拾花酿春的人,懂得惜花惜时惜当下,
简单的事能够郑重以待,
即使是与一盏茶一餐饭之间的虚度,
也更接近一种禅。
那年月,杭州西湖烟霞岭下翁家山的桂花,
是出了名的娇。
诗人徐志摩每值秋后必去访桂,
吃一碗桂花煮栗子,才能觉出人生的好来。
吃花,2000多年的风雅事了。
花开则赏,花落而食,人的一生何尝不是如此?
落到现世里,便是既能琴棋书画诗酒花,
亦能撸起袖子洗手作羹汤。
但这条路的艰辛,难与外人说。
历史上擅制甜点的董小宛,
曾经也是胸有文章、蛾眉宛转的秦淮八艳。
她太聪慧,看透了朝为红颜,夕为白骨的惨烈,
认准一个人,扑向一场奋不顾身的情事,
就好像那是她一个人的歌舞场。
求仁得仁,她嫁了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
通文墨,懂情趣,亲自打理家事,恭谨待人,
阖家上下无一不赞她,
却无人窥见她的奋力与脆弱。
董小宛这样的女子,
最擅长将琐碎的日常,收拢成温柔的浪漫,
连调出的点心亦可流传后世——
精细白糖、褪壳芝麻、纯净饴糖、
松子、桃仁、麻油加上等面粉制成酥糖,
此被后世称为“董糖”的甜点,
初衷却是她向冒辟疆表达的浓酽爱意。
尽管,在一次次危机关头,她总是被他无情地抛下。
为了那一点点尘世温暖,她拼尽毕生气力,
所得,半是蜜糖半是伤。
或许她一早就勘破人世间的**,
如李碧华借孟婆之口道出的,
“人情世事,不外又酸又咸”…
她那么热衷做糖,大概心里苦,
以这种方式向人们婉言相告世相的残酷,情事的艰难。
食物的命运,与人何其相似,
有衰微,有兴盛,可成盛宴,可为家常。
因食材的不同,做法的迥异,注定走向殊途。
然盛筵必散,唯有朴素的清欢是人间至味,
绵长淡远,可留命以待沧桑的清白相见。
我那北方小城的家乡,水土厚重,
因宋时做过陪都,崇文尚武,讲究的是痛快二字。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是一种人生义气;
大汁大芡,烈火烹油,是一种人生状态,
百千年来,演绎着另一种世态**。
那些起源于民间,丰富于每家每户的菜品,
因注入了平民的智慧,
成为食材简单但配料丰富的“家常菜”。
譬如蒸肉。
杭州的粉蒸肉要有花、有风、有景,
“曲院风荷”的鲜荷叶,
将炒熟的香米粉和猪肉包裹蒸制,
是《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
“如果湘粤一带深目削颊的美人是糖醋排骨,
上海女人就是粉蒸肉”,
粉白丰腴,**全在一个粉字上。
而我们当地的蒸肉,有一种选的是腹肋羊尾,
大火炖熟,煮至烂透,
三寸长条,葱、姜、花椒、盐各司其职,
再入味精、蒜片、酱油、醋、香油,
顺条装入碗内,加少量原汤,上蒸笼。
色红油亮,香酸透烂,味道简单霸道。
物厚料重,说到底不过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简单的食材,巧妙的搭配与运用,
这中间需要多少人事的积累,光***的过手,
一遍遍做着眼前这道菜,一道道功夫的琢磨,
不也是人生的写照?
小城的百年老号亦多。
起初,也只是私家菜,
是一个人的口味,一个家族的继承。
许是为了糊口,为了养家,为了有个生计,
谁也不知道路能走到哪去,
明天会怎样,更好或者更坏,
一点点改善技艺,一点点纠错,一点点打磨初心,
所有的功成与声名,也都是靠熬。
熬着汤煮,熬着火候,熬着时间,
熬着内心的甘与不甘,是百千种孤独所成就。
是一代代的人,颠沛流离的过往,
失败后的不甘心,穷途末路后的起死回生,
沉默着,步履不停地,
尝遍五味,识过五色,嗅过五香,
将过程凝练成信仰,
连自己都不曾发觉它自成了一种拔节的力量。
是他们的人生,也是我们的人生。
再简单的食物都有自己的魂魄,
再复杂的食材也不过人间五味,
再长的路途也是一步步获得。
食物承载的是记忆,
记忆里每一步都是我们自己走出的人生。
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一顿毕生难忘的餐饭,
不管身处何方,那才是属于自己的一场沉甸甸的味蕾乡愁。
李舒《**太太的厨房》里,
写每天被起士林面包香味唤醒的张爱玲,
念念不忘童年的一道美味鸭舌小萝卜汤:
“咬住鸭舌头根上的一只小扁骨头,往外一抽抽出来,
像拔鞋拔,汤里的鸭舌头淡白色,非常清腴嫩滑。”
她不会做饭,也不常下厨,却是地道吃货一枚,
连胡兰成都形容张爱玲,
“每天必吃点心,她调养自己像只红嘴绿鹦哥”。
可她之后离家去国,孤独终老,异乡的她,
“着魔似的寻找着上海时的吃食…
她不得不强迫自己戒食绿豆糯糕,南枣核桃糕,
而只能在超市里买华人做的葱油饼,真正的委曲求全”。
羁客方知旧味长。
家乡食物的因子早已被埋在了体内,缓慢生长,
成了一个人的精神原乡。
无论走得多久多远,略一愣怔,
便会想起母亲的那碗手擀面;
是午夜梦回的山河归途,
为着日后的孤独储备一个丰盛的过往,
哪怕是吉光片羽的韶光。
父亲记忆中,那个60年代的深夜,
风声鹤唳,小城清寒,
饥饿与不知名的恐惧,使那样的夜显得疲累幽长,
守着屋内昏黄的光,感到人世莽莽,看不见来路。
爷爷回家,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烧饼,递给才几岁的父亲。
烧饼是半凉的,芝麻稀疏,却不减它的香气,
那一刻父亲记了一辈子。
很多年过去,奶奶走了,爷爷也去了,
父亲还记得清微细的画面。
暖**贫的往事,他反复回想,
有时手里捏着半块烧饼,忽然沉默不说话,
半晌,才传来一声叹息。
我听着,觉得像是从他记忆深处发出来的。
那一刻的滋味,我后来懂了。
年少的我一向听话懂事,零星几次出格的时候。
初中的晚自习后,跟着同学跑到城外看烟火,
课业和晚饭都忘了,待醒觉时,天色已经浓得化不开。
我拽着步子往家走,路过校门时,
看到母亲已推着车等在那里,应该很久了,
一向温和的她,第一次冲我发了火。
回到家,电视机开着,门也没锁,
客厅桌上放着一碗西红柿鸡蛋面,那是给我的晚饭。
细碎的葱花,紫菜几片,香油点点,
碗里窝着一个白白的荷包蛋。
我低头吃面,母亲坐在我对面,一声不吭,
像是对刚才向我发火的自责。
我终于不再倔着,任由眼泪滚进碗里。
此后很多年,那味道死死跟着我。
结婚,生子,高兴,难过,在每一个人生节点和疲累日常,
母亲做的一碗鸡蛋面,便是我的铠甲和软肋,
令我恻然,给我安慰,
使我打起精神面对生活的一次又一次**。
这便是食物的魅力吧,
不仅在于使我们饱腹,更在于令我们柔韧。
外部世界如何强硬,世路怎样残酷,
面对生活赠予的辛辣或寡淡,
也唯有低下头去,不作声张地吃下眼前这碗饭。
李修文说,活在凡俗的日常里,更多时候,
我们要的只是一蔬一饭,而不是救命稻草,
稻草多了,造化多了,都会压垮自己。
到头来都不过海面上的幻影一场。
只有用心吃下的一蔬一饭是我们的信与命,
人生伏线千里,皆始于常情。
算算余生的长度,人心会不会知止?
好好虚度时光新书《何为理想生活》
全网开售
新书购买链接:
随便看看
- 2022-06-29嘿凤梨!金色的它,甜过荔枝
- 2022-05-21美好生活推荐官
- 2021-07-12Windows11激活码和安装密钥共享有吸引力的工具Pro测试
- 2022-05-31金融“贷”动“椒”阳似火
- 2021-07-12windows11配置要求详细介绍
- 2021-07-12大多数符合条件的设备Win11升级将于2022年初完成
- 2021-07-12Windows11如何关闭Win11系统关闭方法
- 2022-05-21等了半年,这台空气炸锅的价格跌了 200 多|A 口袋
- 2022-05-24酒文化馥郁飘香,5.23馥郁节丰德酒业和内参酒官宣了
- 2021-07-12Win7 我还能升级吗 Win11 微软Win11 升级条件和详细信息